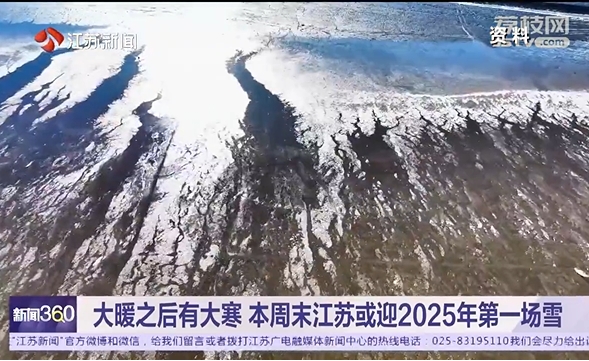□ 本报记者 冯圆芳
年前,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从外地旅行回到南京,稍事休整后,他携全家一起回到海安市过年。
从前,咸带鱼和猪头是海安的过年“标配”。买猪头、褪猪毛,到煨猪头、拆猪头,整个过程充满知识、充满期待、逐步升华、终至高潮。“穷年一定要富过,而且要从心里觉得富,要从心里透着喜庆和虔诚。”——那些年,爷爷的“名言”照亮了贫瘠的日子。爷爷说得最精辟的,要数那句“过年就是把日子过一遍”。“因为年是日常生活的浓缩、精华和辉煌。”汪政解释,“一个人不管活多长,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都在年里面。”
就拿年俗来说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要喝腊八粥,通过享用地里长出的庄稼,铭记庄稼对我们的恩情。腊月二十四掸尘,寓意除旧布新,屋子一新,人的心里也就亮堂了。除夕祭祖,这是慎终追远,不忘来路。年初一拜年走亲戚,中国乡村的社会根基建立在血缘纽带上,这根带子一定要系牢。送灶迎灶是过年的重要仪式,因为民以食为天。有趣的是老祖宗过年也不会忘了鸡、犬、猪、羊、牛、马这些动物牲畜,它们都有自己的“专属节日”:大年初一叫鸡日,大年初二是狗日,初七才是“人日”。鸡放在第一天,因为鸡鸣象征着时间的开始。
年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时间。在传统中国人的循环时间观中,年是律回春渐、一元复始,是新一轮时间的开启。“过年体现了我们对时间的珍视、敬畏,以及对时间的管理:把时间守住了,生命才有价值。”汪政说。
一些地区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冬至标志着寒冷时节将至,杜甫在《小至》中写道,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”,因此冬至的意义特殊。汪政讲起一桩趣事: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是江苏太仓人,冬至那天受邀参加活动,为此老人颇为不满:冬至就是过年,过年怎么能不在家呢!
年,是中国文化的“全本戏”。郭文斌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农历》中,以文学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的节令文化,他关于“文化全本戏”的说法,引得汪政赞同。“春联、门神、年夜饭,这是物质民俗;阖家团圆、走亲戚,这是社会民俗;远思扬祖宗之德,近思盖父母之愆,上思报国之恩,下思造家之福,这是信仰民俗;春联和拜年的语言艺术,一箩筐又一箩筐的吉祥话,这是语言民俗。”汪政感叹,人与自然,人与社会,人与自我,人与彼岸世界,我们生活的哪个维度老祖宗没考虑到呢?
“愿除旧妄生新意,端与新年日日新。”近些年汪政一直在思考,如何创造新的年。
为何要创造新的年?因为年源于生活,是“把日子过一遍”。“当社会发生转型,我们的生活经验改变,就需要把新的经验、文化、审美、心理,予以符号化、审美化,重新表现在年里,彰显我们的文明本质。这对中华民族来说,是新的文化使命。”
非遗传承,见人见物见生活,春节同样如此。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、“非遗热”掀起,但在汪政看来还不够。因为春节不仅是年俗知识意义上的,也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,我们要把年镶嵌在生活中,和时代一起朝前走。年要生生不息,也要返本开新。“过一个创新创造的年,用中国节日、中式美学凝聚Z世代,在全球化语境中强化我们的文化认同、地方认同、国家认同,甚至以‘中国年’对话世界、连接中西,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。”汪政描绘出一幅动人的图景。
又到了儿孙绕膝的团圆时节。看着外孙女淼淼,汪政想起爷爷的老话儿和在他带领下度过的那些丰饶有趣的年。爷爷大字不识几个,却最有文化、最懂生活。对家族的后代,汪政感到一种责任,那就是接力讲好传统文化故事,让孩子们成为有根性的人。他说,身为中国人,就要把“年”过出仪式感,过出味道,过出意义,过出当今中国人的精气神。